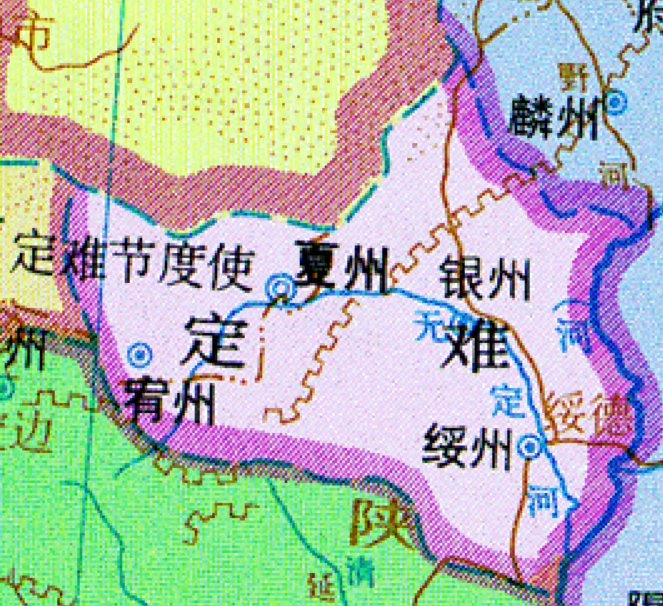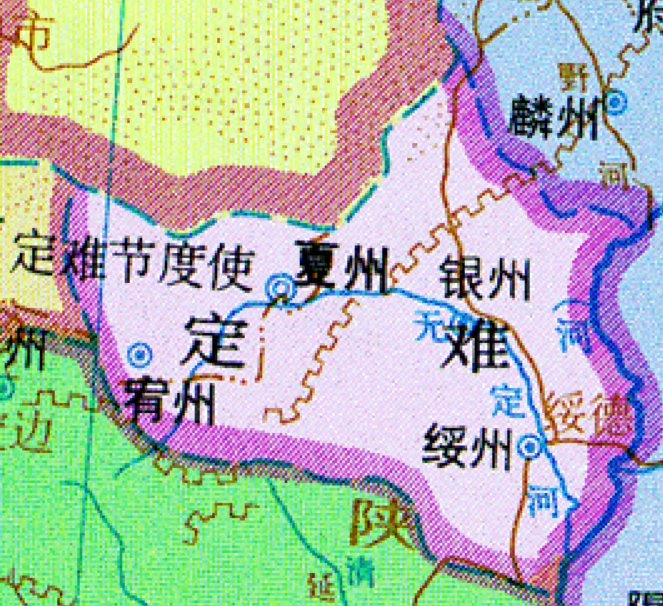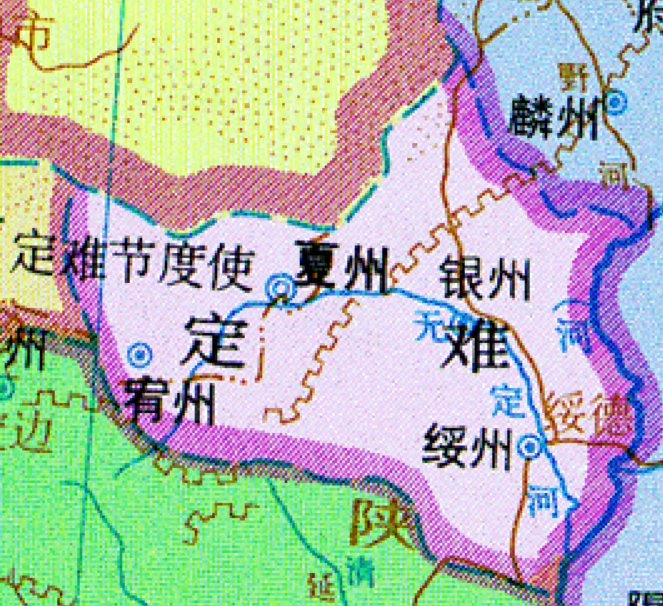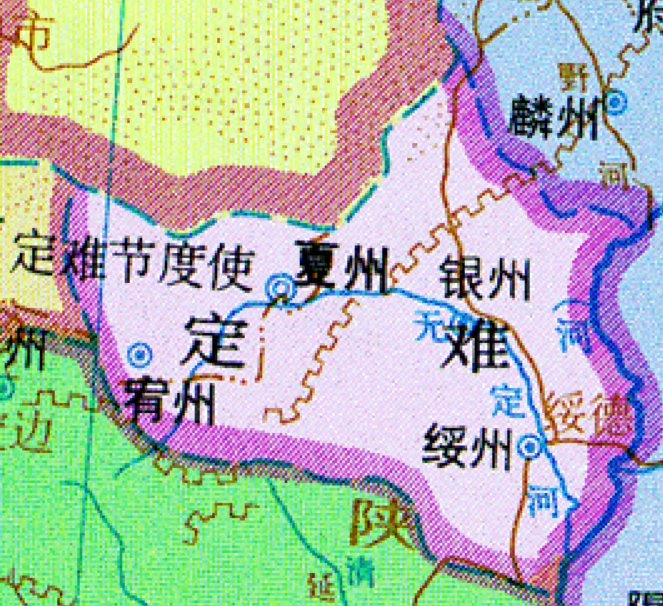第一回 为已逝王女献上的17.5重奏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是万里无云清爽的一天,平凡的生活总是缺乏改变,日复一日的从不知何时持续到现在。对于刘钦瑞而言,迄今最大的波澜就是中考的失利,本来这个成绩是相当出彩的,但可恨的在于它与省第六中学的分数线只差半分。虽然县一中也是不错的选择,但省六毕竟是全国重点学校,乃至不少外侨的子弟在其中就读,刘钦瑞自学过英国的《新概念英语》,一口流利的伦敦腔常让人误会他是致公党,如果有与真正的外国人接触的机会他是绝不会错过的。
他骑着心爱的永久牌自行车来到中书省受降城市兴华区南一环路二号即省六门口打算摄几张照片,但门口的一张海报却把他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哦,原来省六打算兴办侨民班,而且出于沟通或是什么的缘故打算再招收两名本国学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刘钦瑞立马大步流星地直奔校长室开始毛遂自荐,时任校长仔细阅读他的成绩单和简历后便钦定为人选。走出一中时他翩翩起舞,心花怒放可见一斑。
之后的一个月他时不时会设想另一个入选侨民班幸运儿会是怎样的一个人,是男是女,性格如何,会不会和他一样是个化学狂热者……八月的时光在他的眼里流逝得比想象得要快,撕下的日历在红糖冰粉和化学试剂间飞散。
那个星期一终于到来了。凌晨五点二十,刘钦瑞给自己车胎打满气,检查了军绿挎包中齐全的化学试剂,又想起他前些日子电镀过银的飞刀,便随手拿上几把和那些硝酸、铵水之流放在一起,检查一下腕上的电子表,还不到五点半。从北店镇出发,沿省道向北,晨阳刚从华北平原的边际探出头来,把阳光倾泻到他崭新的着装上,伴随着他走过之光县城,走过荣军医院,到南一环口右拐,一侧是化工二厂高耸入云的设备与烟囱,一侧是六中租借给个体户们开设的门店,绕过一枚邮筒,便是省六的大门,架设在门口的机械钟指向六点整。他把车子锁在教职工停车区,遵循雕塑下的指示牌,来到教学楼顶层最东侧的阳面,推开实木打制的门。没想到讲台上坐着一位金发碧眼的高挑青年,听见吱哑的声音,微笑着扭头看向门外的刘钦瑞。
没想到还会有比他来得更早的学生,刘钦瑞心里正在衡量这家伙是昂撒还是斯拉夫,没想到对方更耐不住寂寞,开口就是流利标准的官话:“你好,我叫布尔坚科·安纳贝拉尔,是从苏联来的。”苏联已经没了快六年了,他依然采用苏联作为说辞而非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必定有他自己的考虑在其中,而刘钦瑞却犯了傻,竟直接搭讪道:“刘钦瑞。为什么不直接报真实的国名呢?要知道苏联已经解体多时了。”布尔坚科脸上洋溢的笑容倏地消失了,用强压着悲苦的语气说道:“我就是苏联人!独立出来的这个甚么国不是我的祖国,现在不是,以后永远也不会是!”说完便夺门狂奔而出。
刘钦瑞在原地僵住了,他并不清楚自己的那句话讲得不得体伤害了这位国际朋友脆弱的心灵,哪怕他只吐出了十六个字。正在斟酌反思自己的言辞的片刻,哐当一声,门被踹开了。一个梳着平头带着圆框眼镜的少年以田径比赛似的动作一步一蹦地窜了进来,讲台挂到他的衣角,随即与窗玻璃来了一个亲密接触。刘钦瑞还没来得及前去问候,那个人便从地上捡起自己的眼镜,一壁戴一壁扭头向刘钦瑞道:“呀,另一个同胞已经来啦?咱们都勤奋积极得很啊!我是张叔夜,化学电源厂书记张苏泉的儿子,幸会啊!”刘钦瑞给他打了招呼,不知为何却有了莫名的失落感,可能是他之前预设过这位同胞的形象可能会是怎样一个理想的形象,但这就在两人相遇后直截破灭了。
随着校门处机械钟指针的旋转,太阳离着东面田野的边际线越来越远,这些前来就读的侨民子弟们陆续的走进了这间教室,各色的发与瞳使得从门口看去屋内的光景简直是一幅水彩泼洒的过分的画作。刘钦瑞不时地给诸新同学寒暄几句,这些子弟的官话水平都一流,是他所未曾料到的。低头看了不下十回手表后,他看见一位身材挺拔的年青小伙从前门走来,穿一身前卫而得体的服装,端着部当下最时髦的翻盖移动电话,正和不知哪位学校领导沟通什么事宜。走到讲台旁,驻足四分钟余才挂断,击掌三声示意台下聒噪的各色学子们安静,道:“各位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们,我在这里代表中书省立第六中学欢迎大家前来就读!我是大家以后的班主任张朝曦,三年前刚从中南工学院毕业,虽然已经教了一届学生,但当班主任还是头回,而且还是侨民班的重任。大家相逢即是缘,接下来的三年会使我们共同成长的时光,希望各位同学们不要见外,希望我能成为大家的良师益友!”台下掌声雷起,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子们对这位教师都产生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后来的经历告诉他们这正确得毋庸置疑。
之后便是军训,得益于受降城“双拥”的福利,省六请来驻扎的十九路军五十七摩步旅的官兵承担这份工作,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战士,把军训中的每个项目都办理得光华焕发。很多奇妙的项目是前人与后人都未曾经历的,而侨民班的子弟们也都发挥出从家乡带来的特长。譬如马术训练时布尔坚科骑得稳健潇洒,活像红军的哥萨克,连教官都对这技术自惭形秽。即使没有技术,张叔夜也留下一张在核生化演练里穿简陋的防护服,端56-1冲锋枪英勇冲锋的照相,直到多年后依然嵌在他书桌上的相框里。
短暂的军训结束后便是正式的学期,第一节化学课上经验丰富但忘性颇大的老师张淮北本来想演示氯化氢和氨气的生烟反应,却发觉自己的浓氨水还在实验楼二层的器材室中,刘钦瑞自知这是绝妙的时机,迅速打开地上的挎包,掏出自备浓氨水道:“老师,不打紧!我这里有浓氨水!”张淮北从教多年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心花怒放地请刘钦瑞上台亲自演示。刘在演示时还不忘向台下发文:“同学们知晓氨水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吗?”便开始详述自己对氨水乃至基础无机化学的广博了解。同学们听得都入了迷,刘钦瑞又拿其它试剂演示了几个颇具趣味的实验,可谓抢尽老师风头,台下掌声更连累不断。然张淮北却得意,下课后叫刘钦瑞到办公室,问询他对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意向,刘钦瑞直言自己从初中就寻机会参与这场比赛,从他手中借走几本竞赛的指南教材,得意地回到教室。
午休时间,刘钦瑞走到食堂要了份凉粉,又主动多加两勺辣椒油,再买上一杯凉茶,拢共花去三元饭票,吃得出了满身汗。抬头见对面矮瘦的学生正一手端旧版甲种生物学课本,一手执圆珠笔勾画重点字段。难掩心中好奇,刘钦瑞率先搭讪道:“同学,为什么你吃完饭还在这学习啊?教室不比这更宁静?”那人放下手中的书与笔,道:“我在等我的同学,他约好要和我一起打羽毛球的。”“等人还不忘学习,真勤奋!我叫刘钦瑞,侨民班的,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韩德让,实验一三九班的。”远处一个高而瘦的眼镜拎着一套羽毛球拍走过来,韩德让站起来道:“这位是闫正德,我先走啦。”“刘钦瑞,有机会来侨民班找我玩。”两人走远,刘钦瑞才想起自己碗筷还没归位到洗碗池前。把这项工作完成后,他大步流星地跨出了食堂。
他一边走一边想:“张叔夜一下课就见不到人影了,他能跑到哪里去呢?”片刻后他便把这疑惑抛诸脑后了。不远处几个看上去凶神恶煞的家伙抬着一个瘦削的青年,掷之入垃圾桶中,后又刻意往里丢了许多垃圾。“这不是欺负人嘛?!”怒火点燃了刘钦瑞心中见义勇为的精神,三步并作两步,叱道:“你们这些社会闲散怎么敢欺负到校内学子头上来的?”其中一个满脸麻子的家伙转头瞥了他一眼,道:“臭小子少管闲事,否则连你一起揍!”刘钦瑞伫立原地不动,混混们认定这是挑衅,便要向这看上去温文尔雅的脸上添点彩。说时迟那时快,随着倏地一声,一道锋利白光飞去,划过冲在最前面那泼皮的右肩,叮一声钉在不远处水泥墙上。此人感到肩头一阵冷痛,随即温热起来,几人回首看向墙面,寒光逼人的镀银飞刀楔在墙上,歘地起了冷汗一层。为首受创的便回头道:“老大,遇见硬茬了,撤吗?”另一人回道:“怂甚么?咱人多势众,还怕他一介书生?”几人便执腰间酒瓶撬杠钢管之流前来一决高下,不料刘钦瑞扔下挎包,动若脱兔地避开了每一个攻击,三拳五脚便把几个混混撂倒在地,打得几人直呼饶命。“快滚!”随着刘钦瑞最后的两个字,几位混混落荒而逃。
刘钦瑞没心思去追几个混混,连忙走到垃圾桶前,不顾熏天的恶气和积年的污秽,把上层垃圾刨开,见着一身黑褂黑裤,五短身材,一脸忠良像而挂彩的青年晕厥着。刘钦瑞将之抬到周围地上好一段时间后他方才苏生过来,见到这个陌生的救命恩人,口中“阿里噶多”讲个不停。刘钦瑞晓得了他是东瀛来客,跑到远处拎了桶自来水过来,道:“朋友,快洗一洗吧,那群泼皮无赖是怎地找上你的?”那人好似突然想起什么,连忙说:“我这侧不着急,但是,在我身底下还有一个人哪!”于是刘钦瑞又刨起垃圾来。一位早已昏厥的少女,红棕的长发用赤蓝白紫四色绸带扎成高马尾,身材丰满颀长,着一袭黄褂白裙。虽已是为污秽所侵染,但仍不失为俊俏之姿。刘钦瑞思索唤醒她的方法时,那小伙从垃圾里刨出自己礼帽,灵机一动抬起那自来水泼洒到她身上,姑娘打个激灵,兀地苏醒过来,头脑昏乱着不知自己经历的前因后果。
“我领你们去诊所看看,还是去大众浴池洗刷洗刷?”刘钦瑞向两位发问,“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怎的惹了那群泼皮无赖了?”那青年粗略地洗了手脸,道:“谢过恩人了,我是日侨,名叫宇佐见世文的,出身神秘学家庭,但我是共青团员!”少女从垃圾桶中检出一柄桃木宝剑,跟腔:“我叫冴月麟,是中日混血,父亲是矿路官员,母亲是剑士冴月紫扉帝的直系后人。”“这么讲,那群校外的泼皮无赖,是......”“不错,我和麟本就是侨民班的学生,本是因私事贻误了军训的时机,方才在今日里来校报到。未承想隔着矮墙就翻过几个凶神恶煞的,上来就是拳脚相向,之后的事情想必足下也目睹了吧。”“他们的话太伤人了,直接称我是混血杂种,称世文是畜牲,还说他们是清理垃圾......”“真是无耻的说词!《李德胜文论笺疏》上都说‘我们两国人的共同敌人是法西斯分子和民族败类’,这群泼皮真是有悖先人教导,愧对祖宗!”情绪化的言辞休絮烦,只见刘钦瑞领上两人道:“这时分已经锁了正门,我晓得一隅矮墙,咱们翻出去,我请你们去诊所察看,再到浴池洗刷,如何?”二人点头。
于是刘钦瑞率两人到老校门旁大槐树下,树梢上突然传来熟悉的嗓音道:“嘿!钦瑞!好哥们!过来帮个忙!”抬头一看,张叔夜被双肩书包挂在树梢上动掸不得,道:“我翻出去买了些磁带、光盘之类的,回来时一个不小心使得背包挂树梢啦!来帮忙踹两下树啊!”刘钦瑞前去连踹了十数次毫无收效。“我来!”麟挥手示意他躲开,如武打电影一壁飞踢去,张叔夜在树枝猛烈摇晃下应声落地,不顾率先落地尾椎的疼痛,挥手致意道:“谢过这位女侠了——等等,这两位是?”“等我们回来再给你介绍!”刘钦瑞心中对麟的装束生发了捉摸不出的奇怪感,连忙领着两位翻越矮墙到校外去。复行一段路程,刘钦瑞终于感觉出具体别扭的点,按捺不住好奇心地向麟发问:“麟姑娘,怎是打着赤脚?你的鞋子呢?”“我是剑士,徒跣而行是苦修的一部分,从来到这世上就没有穿过鞋子。”这番解释反而使刘钦瑞更是迷惑,不由得对麟的身世起了兴趣。
另一边,张叔夜正前往教室,却感觉有甚么遗落,回头一看,自己的背包赫然还挂在槐树的枝桠上。一声长叹后,张叔夜又冲向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