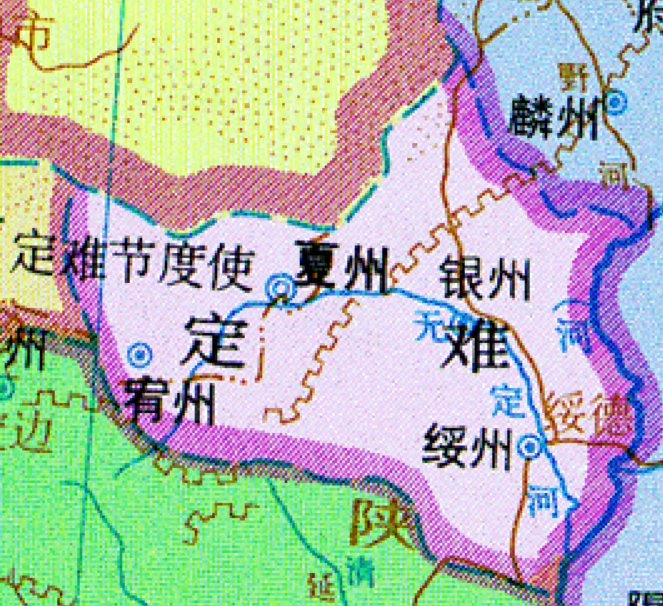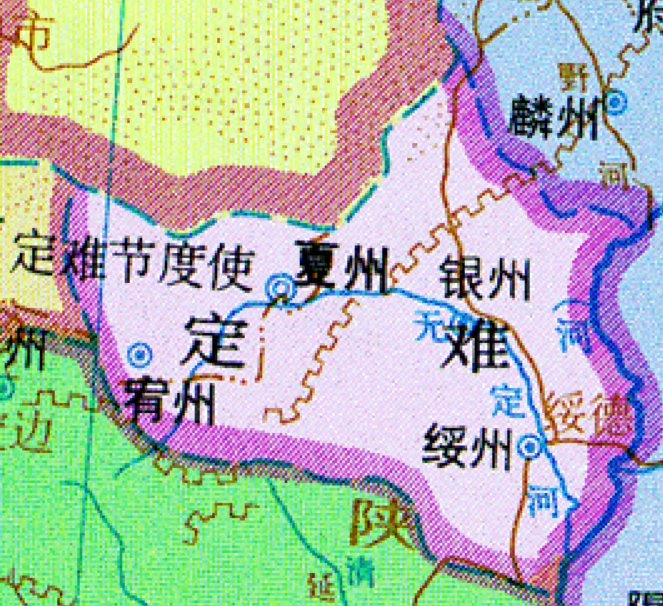(一)
往前某个稍久远的年代,人妖尚不和谐,却并不算那么紧张。人里有个规矩:凡是妖怪不得逗留三日以上,更不得居住。哪怕是最无害的妖精也不例外。
话虽如此,从各番边缘的文献里,仍能发现一个例外——掩埋在历史的尘土里,带着人间之里腐臭气息的人。她叫幽冥地赐,觉妖怪。如今能够打听到的事迹已然模糊,只剩下朦胧的只言片语,似乎是刻意抹去了一般。
我翻过许多烂页,暨幽冥地赐写下的第一篇随笔。那是稗田家大小姐阿弥成人时,她坐在稗田府新腾出的房间里,为阿弥梳妆。
照她的随笔,她和阿弥的关系是不错的。
自随笔的开头,她即写到:她坐在阿弥身后,为新成人的稗田大小姐搭上簪子。氛围格外喜庆,两人却始终兴奋不起来。屋外的人一面催促着,一面招待着来宾。赐倒是不急,她知道老爷们性子急,总归是希望客人留久些,才有时间同他们说客套话,要些份子钱。倒是另一件事让赐忧心......
阿弥年已十六,按照稗田家的传统,该是出嫁的年纪。
赐苦笑起来,低声地调侃道。
“大小姐现在又优雅又漂亮,过两年怕是没人配得上吧”
“那些事,以后再提吧。”阿弥不乐意谈下去。
赐摇摇头,坚持要把这个阿弥不愿提及的话题继续下去。
“时间总会过去的,事情总要面对的,不如趁着年轻,还有机会。多想想,以后也好应对。”
阿弥那是太年轻,不知婚姻意味着什么。一味让赐住嘴,不要再提那些事情。
几番纠缠以后,赐微笑一下,便不再多提。她学阿弥一样不再去想,但逃避恰恰是她最不擅长的事。她越是想,越是烦躁。对命运的揣测时不时从脑海或梦中闪过,对阿弥的忧虑也随思潮涌来。
那年夏天的人间之里很怪。若是说热闹,似乎谈不上,生意好的只有井婆娘的包子店。凡是肉与药材之类,老板大都摇着扇子,看着别人一个个走过去。若是说冷清,倒好像也不至于。老爷们那段时间刚收完税,几个公子还带着佣仆招摇过市呢。马蹄声阵阵,太阳可称毒辣,肉铺店家都不用赶苍蝇,蚊虫自然热死在了外头。高温牵动怒火的老爷大发雷霆,斥责起那些光脚跑步的车夫。
阿弥偏偏在那时有了逛街的心思。赐自然要陪着,却并不情愿。
到街上去,赐用两层麻布把自己裹得像粽子,两条缝出来的袖子拖在地上,时时发出“呲呲”声。手里抱着包裹,里面裹的是觉之瞳。阿弥穿得华丽,玉绿色绣花纹的和服跟荒原开的野草似的,分散着那些投向赐的目光。
路上到处有孩子在跑,他们脚底搭着大小不大统一的破鞋子,含着指头看着进带一个囚犯的大小姐逛街,暗地里编造起颓唐的故事。
他们还想象着为什么会有一个看着并不比自己大多少岁的姐姐会有那身衣服,被广泛认同的解释是:那是天上来的仙女。
赐热得头昏,一路走下去,嘴也不张一下。
一家肉铺边,一个孩子,一个老婆子,自远处望过去就能看到他们在叽叽喳喳吵些什么。店家搭着哈欠,扇子摇得飞快,顺带还用手挑动一下铺子上的鸡腿肉。老婆子扯着孩子直摇头,还打她的手,不计公众影响地叫骂起来。孩子似乎是饿了,只等着肉咬指头。
阿弥在那停留了,有些可怜孩子。
“小赐,还有余钱吗?”她问。
赐没回话,自从口袋里掏了些钱给她们送了上去。
老婆子见有个女人走上来,手里吊着一串铜钱,扯着干嗓子和她说,“给他买些好的吧”。最开始她还顿一下,但见小孩子盯着那串钱,看到赐一身破麻布以后也不闹了,心里萌生些怀疑。生怕这钱拿了,明天瘟神就到她家门口,弄得她好不安生......于是闹的变成了老婆子,几番污言秽语砸在赐身上,她也没半点反应。仍说:“给他买些好的吧。”后面的阿弥叹了两口气。
“娘样鸭滴,死妖怪。”觉之瞳从麻布的缝隙里看到一句心声。
霎那间觉妖怪全身神经都麻木了。纵然实际那话并非专指她,只是人里乡民对怪胎的统一蔑称罢了。她的脸在抽,不再说话,心里还颤颤地念叨着“她说......什么?”
小孩咬着拇指头,也一脸迷惑。
直到阿弥走上去,和老人家浅浅谈了几句。赐没听清。大抵是稗田家绿色的和服和家徽太标致,老婆子认了出来。前一下子还在叫骂,马上就说起她家的好话,笑嘻嘻收了钱。
赐不高兴——浑然觉得妖怪的气场藏不住,注定过不上舒坦日子。
阿弥看着。老婆子扯起咬鸡腿的孩子的袖子,渐行渐远,落成长街上的一处点,日光一抹即去。赐愣在原地,抱着觉之瞳,呆木似的立着,知道阿弥拍了拍她的肩膀,微笑着拉住手。不可名状的颤抖袭击了她。
那天晚上回去,她辗转反侧,不入梦乡,心里总有挥之不去的烦躁。于是乎她从草席上爬起,抽了席子下的几张纸和一支笔,彻夜写起即兴的随笔。依照原本,她大抵没改一个字迹。
打字打的好累呐,这篇文章有八个小节,第一小节共1714个字,打了将近四十七分钟()
未来再补齐剩下的小节吧。